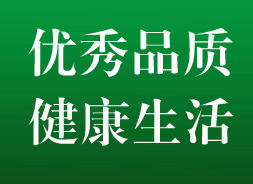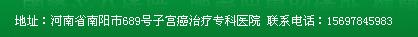顾大才子家在哪里
早上开车送走大姐,这个团圆年,就算真正意义上的过完了。
父母回到故乡,姐姐们又开始新一年的忙碌,就连外甥外甥女,都各自回到了学校。我的世界,重回只有“我”的世界。
1. 思乡派
薛舅。薛舅是我老家东山村,思乡派代表人物。他有五十了,一直单身,俗称光棍儿,父母也在早些年去世,落得一个人生活。薛舅曾尝试到外地打工,却都不曾超过半个月,想家。
最近的一次,小弟在北京承包了物业的一些工程,雇薛舅来打工,干了十几天,薛舅要求回家,理由是想家。小弟觉得不可思议:想家?想谁啊?家里有谁?回家不也是你自己吗?
薛舅不容质疑:没想谁,就是想家,我得回家。
形单影只的薛舅,三间土房子都要塌了,还是大队扶助修葺,才算有了个不漏雨的窝。但只要薛舅说想家,就必须回家,任凭你给他多少好处,都无法阻拦。这可真是,金窝银窝不如他那个土窝。
这次回家,见到薛舅,他因患眼疾失去了一只眼睛,常年戴着一副墨镜。在家的薛舅,虽是个光棍,但过得非常快乐,你细心观察他,几乎每隔几分钟,就能看到他张嘴笑,坐在桌前炸金花,一元钱的赌注,能乐得前仰后合。
在家的薛舅,是“光棍好,光棍乐,光棍的好处说也说不完”;在外的薛舅,是“光棍想家,你们不懂”。
八叔。八叔是我父亲的弟弟,行八。我读初中时,第一次离家,每日熄灯后,躺在康中的大通铺上蒙着毛巾,以泪洗面,想家。我一次次跑回家,遇见在偏房和父亲擀毡子的八叔,他冲我说:男子汉,想啥家,没出息。
我顶撞八叔:你又没读过初中,你怎么知道不会想家?
要不是我父亲抄起了铺毡子的散子向我怒目,我非要和八叔理论清楚想家的苦不可。
年前,八叔的儿子,行四,我四弟,把八叔和八婶接到北京生活。八叔亲自体会到了想家的滋味,隔三差五闹着要回家,把四弟弄得哭笑不得。
一日夜里十点多,八叔又闹着回老家。
四弟苦劝:回家做啥去,城里什么都有,不比家里强吗?
八叔回道:我就感觉家里好,城里这高楼大厦的我看着就难受,出门全是车,哪都找不到哪,晕头转向,还是家里好,我要回家,你开车送我回去。
八叔的脾气挺倔的,四弟无奈了:这都几点了,明天我送你去。
八叔看穿了四弟的缓兵之计:你才不会送我呢,我自己走。
八叔收拾东西,背着小包,四弟拽都拽不住。
八叔变往外走边嘀咕:我有钱,我打车回去。
八叔边走边回头用手拍打自己的包:我有钱,我就是要回家。
八叔强调的是不依赖儿子,自己照样能回家。一千多里地,打车回家,也算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了。不是钱的事儿,而是太想家。
想家的八叔,不知会不会想起我初中时,他对我想家的不解。
终于还是劝住了八叔,又过了几个月,八叔渐渐习惯。
这次奶奶去世三周年,我见到八叔,逗他:还想家吗?
八叔冲我嘿嘿笑:不想,想啥家啊,城里啥都有。
八叔的脸上,放羊十几年留下的黑红色逐渐退去,露出年轻人一样白而有光泽的皮肤。
我笑着夸八叔:白了啊,看着年轻了十几岁。
八叔伸手挠头,有些不好意思:白了吗?没有吧?
八叔抬手摸着自己的脸,荡漾着幸福的微笑。
三哥。三哥是我认识的人里,思乡派的重量级人物,在外发展几十年,仍阻挡不住他滚滚的思想之情。
一天夜里,与三哥喝完酒,他无意中摔坏了手机。手机坏了可是个大问题,根据我多次和他喝酒的经验,每次喝多必然是要和老家人打一通电话诉说思乡之苦的。三哥鼓捣了半天,竟然将一个屏幕都不亮的的手机,拨通了老家兄弟的电话。我坐在车里听他讲着电话,后来唱歌,他仍在讲。大约打了两个小时,手机没电了,三哥才作罢。
这还不算完,三哥接着消失了,一群人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他,打电话肯定是关机的,因为手机没电了。那个晚上我们都没睡好,惦记着三哥,就差没报警寻他了。
次日中午,接到了三哥的电话,神奇的三哥,竟然醉酒之后驱车返回了老家敖汉。他说他清醒的时候,就在新惠的大街上了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,但车上也没有别人,断然是自己开回去的。我的天啊,断片的人,开了一千多里地。
2. 离家日
每次离家,最不愿意的是拐过大山旁乡道的那段弯路,当大山变成背景,就意味着离开了东山村,家就越来越远了。
临行前,我去找三叔,他和八叔一样被儿子接到了城里,这次将和我一起返京。我走进三叔家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院干枯了的荒草,能没过膝盖,想走进去都没有下脚之地。三叔房子的门窗被铁皮封着,门口铁皮下方,留有一个半米高的洞。
我喊了一声三叔,三叔在房内应着。我明白他是从那个洞钻进去的,我也俯身钻了进去,心里想着,这个家,想进去,都要钻洞了,变化太大。
屋内,所有的物件,都挂着厚厚的尘土,三叔站在里屋地上,手里拿着个胶丝袋子,门窗封死的屋内光线很暗,看不见三叔的表情。我停下脚步,与三叔对望,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以往走进三叔家,迎接我的必然是热腾腾的茶水,香喷喷的瓜子,和三叔三婶满脸的笑容。而今,三叔静静地站在地上,僵硬的表情,脸上写着两个字——难受。
我拿出烟,递给三叔一根,我们点燃,吸着,依然是可怕的寂静,说不出话。烟火在一吸一吐之间闪烁,此刻唯一有生命力的就是这忽明忽暗的烟火,而我和三叔,已不知,身在哪里,家在何处。
三叔锁门,我们相继走出他的“家”,敞开后备箱,三叔将胶丝袋子装进车,我问:装的什么?
三叔又拿出一根烟点上:荞麦皮。
我启动汽车:荞麦皮?做枕头?
三叔吸着烟,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:你三婶说城里的枕头睡着难受,让我带些荞麦皮做枕头瓤。
三叔在东山村的家过得殷实,什么都不缺,而如今,再回来,只能带走一袋荞麦皮。
返京的车,从我家杏树下启动。杏树是我儿时种的,因长得过大,总遮挡屋内阳光,母亲要砍掉,父亲阻拦。父亲说:可不能砍,发山水咱俩还得上树保命呢。
我每次都将车停在这杏树下,如停在我的童年。每次走,也都缓缓在杏树下倒车,杏树结的杏很大很甜,可我已有十几年没吃过了。车缓缓驶出家,我从后视镜看杏树,心里,像吃了还未成熟的杏,酸。
汽车拐上大山旁的乡道,这是东山村的出口,像以往一样,我有想起了那句诗: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3.一个人
大姐走了,我在城里的家,又变成了我一个人。
我走进父母在我家时住的房间,耀眼的阳光打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我想象着父母在时的场景。母亲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太阳,她的冠心病和腰间盘突出都适合晒太阳;父亲躺在床上,听收音机里的评书,声音很大,他耳沉,我在对面房间关着门都能听到。
我走到阳台,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《故事》,躺在躺椅上,晒着太阳,像我母亲一样,将书盖在脸上,回忆着父母在的每一个细节,慢慢地睡去。
醒来的时候,已是中午,有些饿,起身去寻吃的,餐桌上,大姐走时做好的满满的、尖尖的一大盘田螺。田螺是临走前表弟东子送的,还有油滋啦和咸菜嘎达。喝一口啤酒,吃一个田螺,每一口,每一个,都是想家的味道。
朋友说我:你都多大了,还想家。
我说:可能是父母刚走,需要习惯几天。
其实,我时不时都会想家,但我发现一个可怕的现象,即便是回到了故乡,依然还会想家。我找不到家了,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,在城里想故乡,而回到故乡,依然想家。
融不进的城市,回不去的故乡。
三叔说:回到家,看到破破烂烂的,这哪是家,这不是家。
那么,家究竟在哪里?
家在哪里,家就在胶丝袋子里,来自故乡的荞麦皮。
家在哪里,家就在门前的杏树上,回来时是甜的,走的时候是酸的。
家就在村口的乡道上,回来时,大山壮美亲切,离家时,大山痛心悲伤。
乡情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