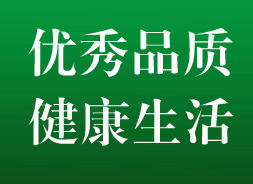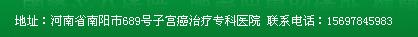饮食文化的意义
近日读了一篇闲文,谈的是不同时期中西方饮食的不同观念。饮食伴随我几十年了,如影随形,一日不曾分开。但是读了此文才对饮食刮目相看。原文太长,学术性也太强,不便转述,下面就说说我的粗浅收获和感想吧,算是读后感。
先说说古代。在文明社会之前,无论中国还是外国,饮食的意义都很简单,就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填饱肚子。填饱肚子只是追求,实际上原始人类相当一部分因食物不足而饿死了,一部分则是饥一顿饱一顿地活了下来。吃什么呢?山上的野果、地里的野菜、河里的鱼、还有捕捉到的陆地动物(多为食草动物,如果遇到食肉动物就说不准谁吃谁了),只要能填饱肚子,吃什么都行。
后来有了农牧业,生产力提高了,有了剩余生活资料,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,饮食就不再那么简单了。什么级别可以吃什么,是明明白白的。慈禧太后每天正餐必须道菜,能吃多少不要紧,不够数就有人掉脑袋了。这是地位的象征。在许多朝代,没有爵位或爵位低的富人再有钱也不能享受公卿的饮食标准,例如杀牛吃肉,就得问罪。
在西方,有些饮食带有宗教色彩,吃什么由神来规定。吃五谷杂粮没有限制,但是吃什么动物就有复杂的教规。比如有的宗教规定:偶蹄并且反刍的动物(如牛羊)可以吃,其它动物(如马、狗、兔子、蛇等)是不可以吃的。基督教反对奢侈,提倡简朴、节欲,还有禁食祈祷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将硬面饼分给弟子说,这是我的肉;又把葡萄酒分给弟子说,这是我的血。想想,人类的食物是上帝赐予的,要怀着感恩的心对待饮食,岂能铺张浪费、暴饮暴食?
如果没有宗教的约束,西方人在饮食上的铺张也是触目惊心的。当年罗马人统治地中海一带以后,希腊信奉的奥林匹斯宗教受到冲击。罗马贵族为了夸耀自己的富有,极尽饕餮之能事,他们的盛宴可以持续10个小时,什么蜜汁松鼠、大象鼻子、天鹅舌头等等,越是珍贵越荣耀。客人吃饱喝足后,为了应付下一道菜,不辜负主人的盛情,就用备好的羽毛刺激喉咙,把肚子里的食物吐出来,漱漱口,接着吃。这时的饮食就具有了财富的意义。多亏罗马帝国是短命的。
中国没有自己原创意义上的真正宗教,就是道家也不反对吃喝。孟子说“食色性也”,充分肯定了饮食的合理性;郦食其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强调了饮食的重要性;孔子说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反映出对于美食的追求。因此中国人在饮食方面下的工夫举世无双,单说中国的八大菜系相比,就足以让西方的厨师目瞪口呆。到了现代,饮食没有了严格的礼法制约,也淡化了宗教的色彩,变得十分自由。只要有钱,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!如果没钱,让我买我也不买(例如阳澄湖大闸蟹)。
一旦饮食失去了宗教、等级的色彩,人们对它的讲究反倒不那么多了。饮食又恢复了它本身的意义,就是吃饱肚子,满足营养需要——当然口味要好。于是饮食开始工业化大规模加工,什么面包、饼干、罐头、香肠、火腿、便当(盒饭)、方便面、啤酒、可口可乐、绿茶、炸鸡腿、炸薯条、三明治、肯德基、麦当劳,遍及世界。饮食趋于便捷化,吃饱就得。
这样一来,饮食原本的功能性增强了,象征性淡化了;共性增强了,个性弱化了。饮食缺少了审美的情调,只剩下单纯的物质价值了。就像养鸡场里配制好的统一饲料,无论哪只鸡都是同样的伙食。可能有的鸡想来点黄瓜,有的鸡想加点胡椒粉,有的鸡想加点山西陈醋,可是通通没人理睬。这样吃饱了又有什么意思呢?于是有些人产生了后现代的审美化饮食追求:自己炒几个可口的小菜,喝点小酒,岂不有滋有味,乐在其中?或者去饭店点几个自己喜欢的菜也比整天吃炸鸡翅有意思。我出差在外就喜欢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,比如去西安尝尝老孙家的羊肉泡馍,到北京尝尝芥末墩,到杭州尝尝西湖醋鱼,到太原吃碗刀削面,到成都涮点九尺鹅肠,到云南尝几个又酸又辣的傣家山野菜,到长沙要一个剁椒鱼头,到乌苏里江尝尝赫哲族的拌生鱼……感觉比大饭店共性的大菜更有情趣。虽然花钱不多,但饮食文化的审美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
如今饮食没有了宗教和等级的光环,但却时常炫耀出财富的色彩。富豪们的盛宴必须与众不同,一定要有燕窝、鱼翅、龙虾之类,如果弄到熊掌、果子狸、穿山甲、鳄鱼蛋,主人的脸上就越发自豪了!好不好吃不要紧,要紧的是挥金如土的豪气——咱有钱!如果黄金可以吃的话,一定会端上一盘鲍汁金条。便是穷人也有浪漫的饮食理想:等我有钱了,买两碗豆浆,喝一碗倒一碗!看来,刚刚回归本色的饮食又要异化了,就像海里的石头,总有一些水草、苔藓、海蛎子附着在上面,让人看不清石头的本色——吃喝到底为了啥?